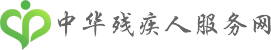山东4残疾人组成乐器乐队,合练仅一月赢得全国一等奖
| 2017年8月18日 | 分享到: | 来源: |

一段简单的序曲结束,唢呐、二胡、板胡、坠胡齐响,欢乐的声音在大剧院里回荡。8月16日下午,在济南省会大剧院,当四位残疾人再次奏响这曲改编后的《洞房花烛》时,整个剧场都被他们打动了。这四个人分别叫高全明、翟春华、魏雅然和王文尧,但从这欢快的音乐中听不出,他们中有两个是盲人,一个弱视、还有一个是肢体残疾。这是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的汇报演出,就在几天前,这个四人组合凭借这一曲《洞房花烛》获得了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东部片区器乐组一等奖。
拉琴30多年,获奖有些意外
16日下午,在省会大剧院后台等待着上场演出,戴着墨镜的高全明看上去十分淡定,自从10岁学习坠胡,到今年已经整整32年了,从来都是在老家高唐街头巷尾卖艺的他,从没想过会登上这么大的舞台,静静地听着前台已经开始的演出,高全明也沉浸在舞台音乐中。

“小时候父母送去学艺,无非是为了学门手艺,好讨口饭吃,自己虽也热爱这个行当,但能登上舞台其实是个意外。”高全明依旧习惯说自己是个街头艺人,尽管这两年参加了几个比赛,拿了几个金奖,但在比赛之后,他依旧会回归街头。“习惯活跃在老百姓之中了。”高全明说。
在这个《洞房花烛》的合奏中,高全明的角色其实是新娘的父亲,要将女儿出嫁的欢喜与忧伤都在坠胡里表现出来,对老高来说,这些都游刃有余。“这些年,习惯了在街头一个人表演,边弹边唱,西河大鼓、山东琴书、河南坠子、山东吕剧……都十分拿手了。”高全明说,虽是盲人,但他感觉自己在音乐上的努力并不差于一般的专业演员。“小时候跟师傅学琴,让你三九天在屋外拉,必须要练到手没知觉了也能把音拉准才能进屋。”
从没进过专业的剧团,但高全明总会沉浸在自己的演奏中,“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、见不到光,但音乐就算是我的光吧,可以用它和任何人交流。”高全明说。
虽是民间艺人,但视音乐如知己
在这个名叫“唢呐与三胡”的演出中,来自济宁鱼台的翟春华就是那个唢呐,与高全明一样带着墨镜,感触不到一丝光亮,但也如高全明一样视音乐如知己。“他们都叫我小孩。”说起话来就如同他在演奏中新郎的角色,带着一些幽默。学吹唢呐15年了,这个30岁的小伙子如今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。被称作队伍里的“大牌”,只是别人不知道,这个大牌的唢呐基本上是自己从录音机里自学的。
“上了两次唢呐学校,一共上了差不多40天,以后就都是自己学了。”翟春华说,学吹唢呐的那年是2002年,他已经15岁了,自学了一年,就加入了一个唢呐班,于是在老家鱼台的红白喜事上,便时常能见到这个带着墨镜的小伙子尽情地吹着唢呐。“这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技能,确实是特别喜欢音乐,音乐就是一个知己,看不到谱子,都是自己一句一句跟着录音机学,要不是真的喜欢,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。”翟春华与乐队里的扮演新郎父亲角色的老乡王文尧一起练习着演奏,俩人十分默契。在今年6月份的全省残疾人艺术汇演中,翟春华得了金奖,右腿有些残疾的王文尧得了铜奖。
“都算是民间艺人吧,算不得专业,但大家都把手里的乐器当做生活里不能缺的伙伴了。”王文尧演奏的是板胡,为了适应《洞房花烛》这个由唢呐曲改编的音乐,已经66岁的他也是拼了老命,“老母亲有病,本来不想来了,但缺了一个人,大家就都没法演出了,毕竟能上一次大舞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”从合练到比赛的时间只有一个月,为了记谱,老王用了10天的时间,“十几页的谱子,没想到能背下来,但为了演出效果,还是把谱架子给避免了。”
最年轻女队友,已是民大大学生
在这个四人团队里,魏雅然是唯一的女生,两只眼睛的视力分别只有0.1和0.06,但化好妆、身着彩裙的她依然光彩照人,她便是四人合奏中的那个新娘了。同样是因今年六月份的比赛结缘,与其他几个纯粹的民间艺人不一样,魏雅然已是中央民族大学二胡表演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。

与化妆室里其他的小姑娘相互鼓励着,魏雅然总是一脸灿烂,只是视力不好,妈妈总要陪在左右。“从五岁开始查出眼睛有问题视力开始逐渐下降,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音乐了,我对音乐是真的喜欢。”演出开始,魏雅然悠扬的二胡声时透出新婚的喜悦,偶尔也流露出一丝离开父母的忧伤,伴随着音乐的起起落落,魏雅然的喜悦表情里也不断有着微妙的变化。“当年参加高考,雅然是以专业第二名的成绩考上的中央民族大学。”妈妈很为这个女儿自豪。当年读高中,雅然看不清试卷和书本,都是妈妈帮她读着学习,看不清乐谱,爸爸专门给她抄大号的。
“因为看不清乐谱,没法合练,以后毕业了很难进入一个乐团工作,但我享受拉起二胡的每一刻。”魏雅然说,与三位哥哥、叔叔的合奏赢得了一等奖,也给她一个很大的鼓舞,“身有残疾并不是个什么障碍,只要是好听的音乐总能打动人。”
文章来源齐鲁壹点